最近在讀一本書,「再會吧!公共人」。
╳ ╳ ╳
有一個朋友的朋友可以說是正面人生的代表,跟我同年的他,其事蹟如果說了出來肯定讓平輩感到尷尬,長輩覺得怎麼沒能多個女兒嫁給他。
他的人生聽起來根本就跟樣板一樣,完全的模範,也同時沒有真實感。他還是朋友的朋友,雖有一面之緣,畢竟我還是不認識他,關於他的事蹟也都是聽友人陳述而來, 同樣的,還是沒有真實感。
某,現育有一女,妻是學生時代的青眉,現在定居在淡水,平日在另一個城市上班。前一個工作在上市公司昇任到管理職,隨後厭倦在他鄉工作便返鄉接任現在的工作。五子登科,就在我現在這個年紀。
某與友人的互動中也常告誡友人,要其將其生活回歸到軌道上。
雖然所用的文字為何,不得而知,卻可以多少嗅到某表現在生活的一個層次上的判斷。
╳ ╳ ╳
以下是一段文字摘錄自「再會吧!公共人」。
18世紀各國首都市民試圖在行為及信仰當中去界定公共生活是什麼、又不是什麼。公與私之間的界線,基本上也用來區隔斯文得體(civility)(以世界主義的、公共行為為代表)與自然(以家庭為代表)。人們認為兩者彼此衝突,但這種看法的複雜之處在於人們不願偏愛其中一方,而是使兩者保持平衡狀態。以一種情感上能滿足自己的方式來與陌生人交涉,但同時又與陌生人保持疏離,18世紀中期的人們認為這種行為能夠讓人類這種動物轉化為一種社會性的存在。於是,成為人生父母、經營深度友誼的能力被認為是自然潛能,而非人為創造之物;人們在公共場合中成為自我,在私領域中實現自己的天性,尤其是藉家庭內的經驗的實現。(1)
╳ ╳ ╳
翻到背面看:
在觀察了解後友人與某的生活價值會有個頗為對立的結論出現。而這中間另外一個有趣事實是:屏除前述的結論,他們這對十幾年的好朋有,平時tone調協調,然,同時也能各自潛入各自的生活。
1)再會吧!公共人(The Fall of Public Man) Richard Sennett 萬毓澤譯 國立編譯館主譯 學群 一版 第一章 第23頁
skip to main |
skip to sidebar
PERHAPS YOU MAY ALSO VISIT
- Flickr
- nobiggy
- MASH
- 貝哥哥指南
- 識得20世紀經典設計
- fixed gear gallery
- Fixed Gear London
- nabiis
- Keirin cycle culture cafe
- team flwrider
- ride!
- UCI世界杯登山車賽
- Jordan Baseman
- Annabelle Craven-Jones
- TopGear
- Radio4
- alta bikes
- John Sypal
- Formula 1
- Leica MP
- Putney
- XL1s
- Wimbledon
- Wimbledon College of Art
- WHITE GOODS
- good4u2
- 隱蔽青年
- 花襲人。花盜人。
- 小北
- 愛的大逃殺
- KIKI
- strid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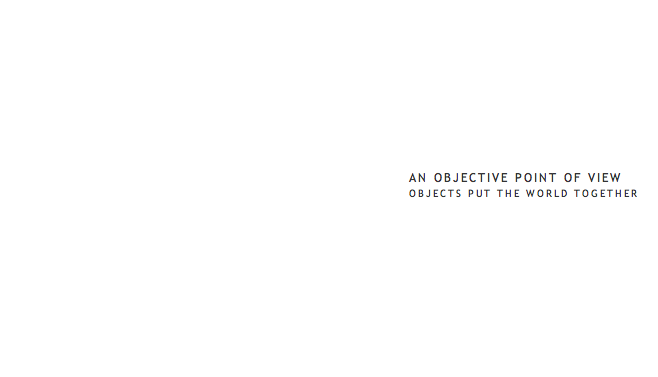



0 意見:
Post a Comment